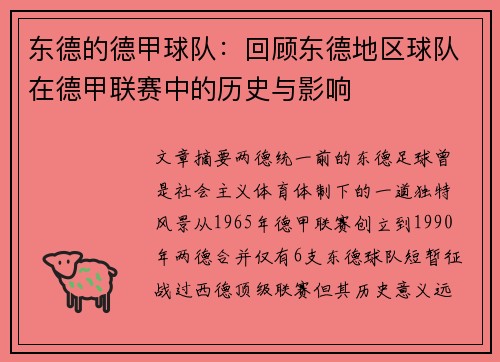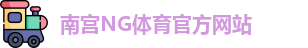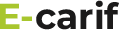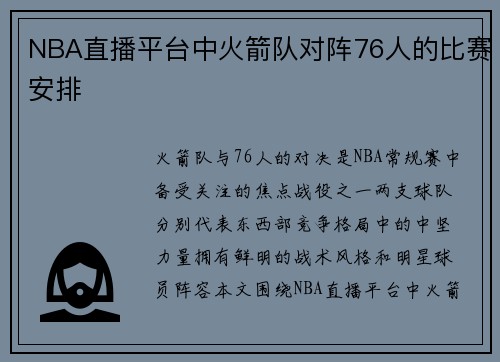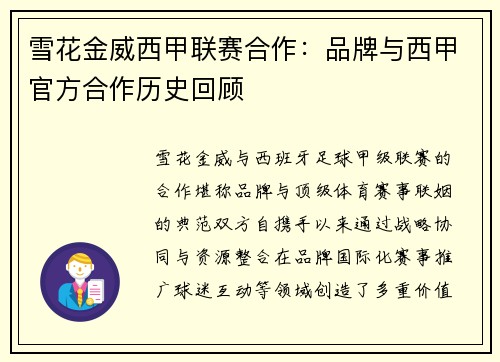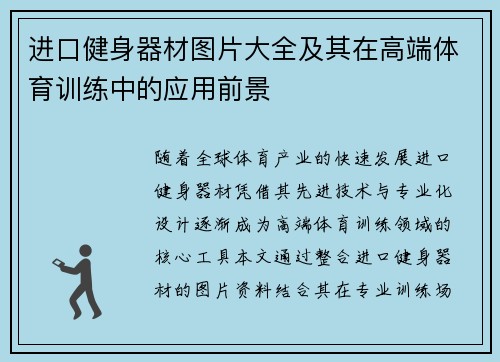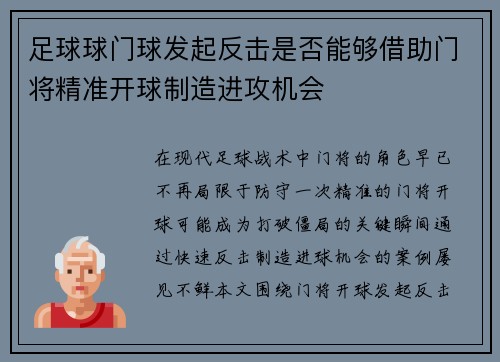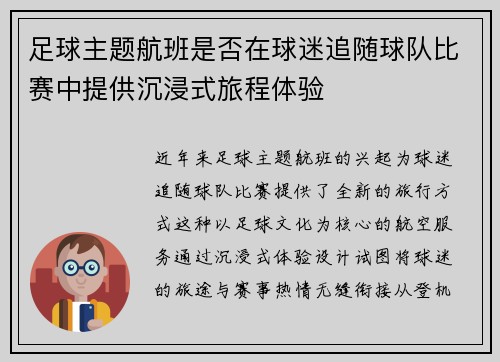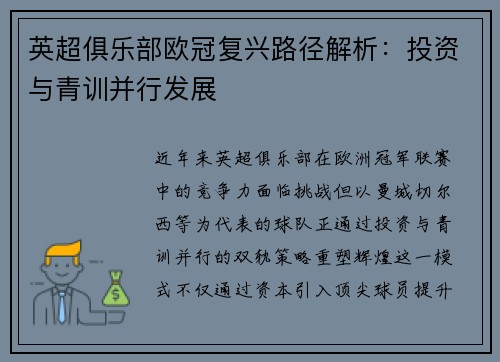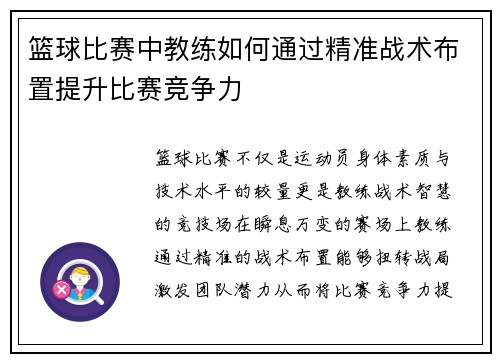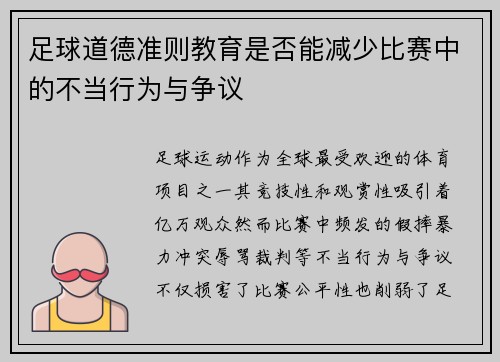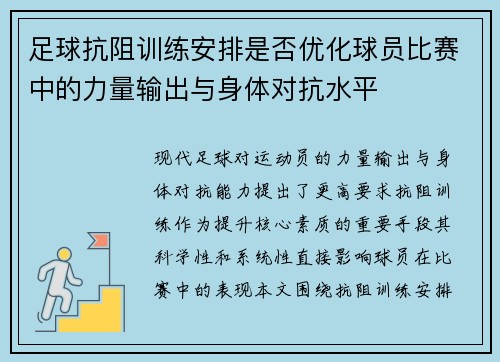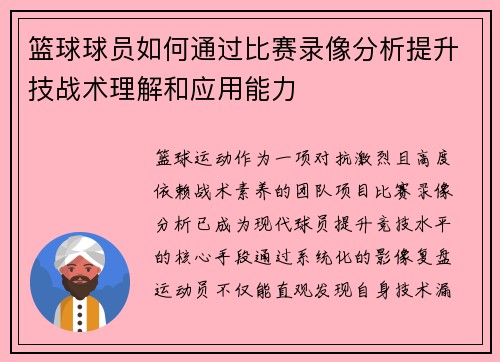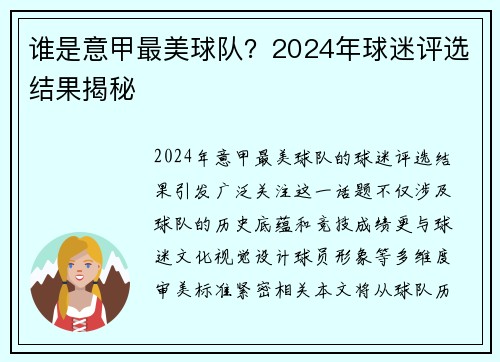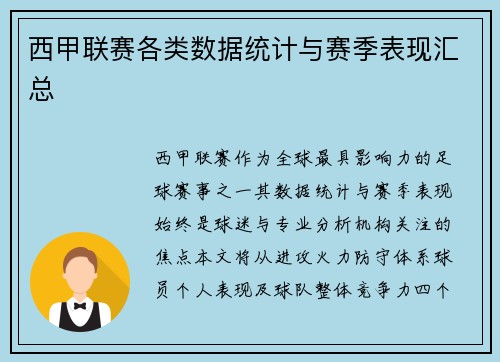文章摘要:
两德统一前的东德足球,曾是社会主义体育体制下的一道独特风景。从1965年德甲联赛创立到1990年两德合并,仅有6支东德球队短暂征战过西德顶级联赛,但其历史意义远超竞技成绩本身。这些球队承载着特殊时代的政治烙印,展现了计划经济与职业足球的碰撞,更在统一后成为东西德文化融合的缩影。德累斯顿迪纳摩、柏林联等俱乐部,既见证过斯塔西特工操控联赛的黑暗岁月,也经历过资本冲击下的生存挣扎。如今,柏林联的崛起为东德足球注入新活力,但地区发展失衡的阴影仍在。本文将从历史脉络、体制特征、竞技表现、社会影响四个维度,解析东德球队在德甲版图中的特殊轨迹。
1、分裂时代的足球格局
1949年德国分裂后,东德建立职业足球联赛体制,但始终与西德保持竞技隔离。1965年西德创立德甲时,东德足协同步推出DDR-Oberliga(东德甲级联赛),采用与西德迥异的半职业化模式。球员需在工厂挂职训练,俱乐部运营依赖国营企业注资,这种体制虽保障了基层青训体系,却限制了职业化发展。
冷战高峰期的1970年代,东德政府将足球视为意识形态战场。斯塔西秘密警察深度介入联赛,德累斯顿迪纳摩因隶属国家安全部,十年间七夺联赛冠军。这种权力干预严重扭曲竞技公平,导致柏林迪纳摩等球队长期受打压。政治操控制约了东德足球水平,其国家队唯一的世界杯经历止步于1974年小组赛。
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夕,东德联赛已陷入系统性危机。球员月薪不足200马克,球场设施严重老化,观众上座率持续下滑。这种体制性困境,为后续东德球队融入德甲埋下隐患。
2、统一初期的艰难转型
1990年两德合并后,东德联赛被整体并入德国足协体系。根据过渡方案,原东德前六名获得德甲/德乙参赛资格。但体制转换带来剧烈震荡,罗斯托克、德累斯顿迪纳摩等传统劲旅,突然面临职业化运营的资金缺口。柏林墙倒塌后,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1:1兑换的政策,使俱乐部债务雪球式膨胀。
竞技层面,东德球队遭遇全方位冲击。德累斯顿迪纳摩在1991/92德甲赛季仅获2胜,创下历史最低积分纪录。球员体能储备、战术素养与西德存在代际差距,青训体系因教练流失陷入瘫痪。更严峻的是人才外流,东德地区每年超200名青少年球员被西德俱乐部挖走。
经济基础薄弱加速了东德球队衰落。至1995年,原东德14支职业队中,仅罗斯托克和科特布斯存活于德甲。企业赞助转向西德市场,莱比锡火车头等百年俱乐部因破产重组消失。这种断崖式衰退,折射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。
3、竞技成绩的起伏曲线
在德甲历史上,东德球队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994/95赛季。罗斯托克队以升班马身份夺得第六名,门将霍夫曼创造单季15场零封纪录。这支以造船厂工人子弟为主的队伍,曾用钢铁防守让拜仁慕尼黑三度折戟。但辉煌如昙花一现,次年即因主力流失跌至保级区。
南宫·NG28欧战赛场更能体现东西差距。德累斯顿迪纳摩1993年征战联盟杯时,主场0-2不敌罗马,暴露出对抗高强度逼抢的短板。科特布斯2000年升级后,连续三个赛季成为德甲"升降机",最高单季积分仅为33分。直到2019年柏林联升入德甲前,东德球队在德甲总胜率不足28%。
值得关注的是区域足球文化韧性。马格德堡队1974年夺得欧洲优胜者杯,至今仍是东德足球的巅峰记忆。柏林联的"钢铁联盟"精神,通过死忠球迷献血筹集升级资金的壮举,创造了现代足球的另类传奇。这些文化基因,成为东德足球复兴的精神火种。
4、社会影响的深层映射
东德球队的兴衰史,本质是两种社会制度碰撞的微观呈现。罗斯托克队主场DKB竞技场,前身是东德时代能容纳10万人的露天体育场,其改造过程中的文物保护争议,凸显了历史记忆的撕裂。俱乐部博物馆里并置的马克思语录与商业赞助板,构成后社会主义时代的特殊景观。
足球场成为政治博弈的延续战场。2014年莱比锡红牛队崛起时,西德球迷集体抵制其"资本足球"模式,而东德民众视其为打破地域歧视的象征。柏林联与科特布斯的"东德德比",观众席常出现前东德国旗,这种怀旧情绪暗含对现实发展失衡的不满。
人才培养体系正在重构。德国足协2002年启动的"东部促进计划",在梅前州建立青训中心。2023年德甲联赛中,东德地区贡献了14%的本土球员,较1990年代提升9个百分点。但顶级球星仍多来自西部,这种结构性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。
总结:
东德球队的德甲征程,是德国现代史的特殊注脚。从计划经济桎梏到市场经济冲击,从意识形态工具到文化认同载体,这些俱乐部承载的已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胜负。罗斯托克的沉浮、柏林联的崛起、莱比锡红牛的争议,共同勾勒出社会转型的复杂图谱。球场上的东西差距,本质是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投射,也是集体记忆重构的战场。
三十余年的融合历程证明,足球领域的真正统一,远比政治版图的合并更为漫长。当柏林联球迷在欧冠赛场高唱"我们永不屈服"时,当莱比锡红牛打破拜仁垄断时,东德足球正在书写新的叙事。这种超越竞技的精神传承,或许才是足球运动最深刻的社会价值。